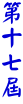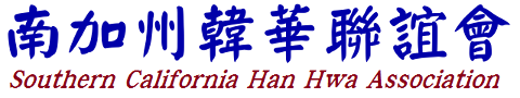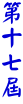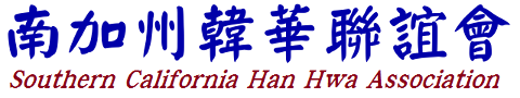|
驀然回首話少年
六二五韓戰以前,黃海道延安市⦅是市是郡是邑待查⦆是南韓地盤,戰後畫出一道三八線,把我的第二故鄉送進北朝鮮的懷抱,頓使我對童年的小故鄉有欲歸不能的創痛與哀傷。
在延安市,父親開設了一家頗有規模的中餐店「延一舘」,生意紅紅火火,一枝獨秀,傲視其他同行。
我年小無知,時常在廚房穿梭,纏著大廚大伯弄點糖肉、炸鷄解饞。有一天大伯從爐灶剛拿下一大壺開水,沒料到我會一下衝到他身旁,滾滾一壺開水無巧不巧碰在我的右肩上,
據說我疼得發出淒厲的叫聲,大家也慌了手腳,急急把我送上醫院,聽說大伯因此辭了工。到今天,我的右肩還留有一個醜醜地大疤呢。延一舘顧用了好多個亭亭玉立,明眸皓齒,
露出俏皮慧黠神韻的女孩,她們常帶領我到街上小攤去買糖果,有時用纖纖玉指揑揑我的臉腮,摸摸我光亮的頭頂,⦅那年代用剃刀剃頭⦆像大姐哄小弟一樣對我愛護備至。她們歌唱得好,
鼓打得好,韓式的舞也跳得好,每當三、五成群客人光臨時,就是她們大顯身手的時刻,熱鬧極了。
在延安,我上的什麼小學,唸的什麼書一點印象沒有,但我卻清楚地記得,每次上体育課時,老師把我們帶到操場一個大圓沙坑,讓大家沿著沙坑圍坐一圈,教導摔角技巧,
或許因為我摔角運動肌肉發達,每每班級比賽都無對手。
我的姨夫和姨母住在大邱,他們是虔誠的基督教徒,姨父還是某教會長老。有一年他們來釜山參加一個各地聯合佈道大會,因為我不上教會,姨父母開導了我整整一個小時,
我恭敬聆聽。姨母忽然問我:你的日本話沒有忘吧?我搖搖頭。她對我說了幾句流俐的日本話,我一下變成了啞吧。她嘆了一氣說:你怎麼把日本話都忘了?多可惜。我默不著聲,
其實我正在暗暗責備自己,真是個大笨瓜!好像前年姨父母來洛城為女兒出嫁辦喜事,還給我來了一個電話,我都忘了問問我小時在延安到底是唸的那一國小學?
因為我姨在延安和我上同一個小學校,只是她比我高一班。兩年來我疏於問候,也不知年邁的倆位老人家近來可好?謹此祝福他們快樂康泰!
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,父親將「延一舘」交給三叔叔經營,我們擧家搬遷到仁川市中央洞,在中央洞買下了一棟日本人的二層樓房。據說那段日子,有些韓國人時常追打日本人,
並強佔日本人的房子,所以日本人都嚇怕了,急著回本國,因此給錢就賣房子,不必討價換價。
算算年令,一九四五年我是十歲,上了仁川小學三年級,誰知三年級的小板櫈還沒坐熱⦅才三天⦆,有一天班導師叫我揹著書包到辦公室,班導師是一位女老師,有個甜美的臉蛋,
細高的身材,笑起來露出兩個深深的酒渦。我到了辦公室,看到父親和校長在說話,班導師和父親打了個招呼說:你這孩子會說一點中國話,但不會寫中國字,
算術有三年級的程度,用日本話可以很流俐地背下小九九歸法,但這沒用,要先學中國字,所以要先轉到一年級去打中文基礎,因學齡大了一點,視學習進度,
我們可以考慮讓他讀完一年級後再回到三年級。就這樣,我這個大個子,每天要羞羞答地低著頭揹著書包走進教室最後排的坐位聽課。
在三年級,我坐在較前排,回頭一掃,後面黑鴉鴉一片大蘿葡頭。在一年級,我坐在最後排,抬望眼,前面黑鴉鴉一片小蘿葡頭。下了班,這些小蘿蔔頭吱吱喳喳吵個沒完沒完了,
我就像掉進鴉鵲窩,耳根從沒得安寧。
有幾個小蘿蔔頭膽子較大,不時盯著我傻笑,我也只好回報一個傻笑,誰知這幾個小蘿葡頭膽子越來越大,有一天竟然爬在我背上耍賴!
日子過得飛快,轉眼讀完一年級,某天,三年級班導師又把我帶回三年級。再度上了三年級,我坐在前面第二排,我前面第一排有兩個小蘿葡頭,一個是沙慶珠,一個是李尚鐸,
以後都成了我的好學友。
我六年級那年,大考考試剛考完,忽然鈴聲大響,是校長緊急召集全體同學集合,說明戰爭已爆發,宣佈停學。這年我十五歲。
韓戰爆發後,經濟無著落,家庭生活一直陷於困境,我十六歲那年,程大叔帶我到大邱東大新洞某餐舘上工,離家時,母親擦著淚水把一個小衣包塞在我手裡,
再三叮嚀我注意不要受了涼,吃飯要吃飽,我也噙著淚向母親道別。
大邱這個小餐舘,廚房兩個人,老板和我,前面堂裏有一位老先生坐鎮,共三個人。
我在廚房洗碗、煮飯、砌菜、拉麵、外出挑水,老先生懶了,還叫我送外賣,他老人家卻噙著煙袋在吞吐,閉著眼睛在唱四郎探母。
到了冬天,我最想家,因為餐舘用水要到房東後園的井去挑,一根粗木棍當扁擔,前後兩端各用鐵鉤掛了一個鐵桶,因桶底生了銹裂了大口子,
好不容打滿一桶水,一路上像噴水池,到了餐舘剩了半桶還不到,我的褲腿、鞋襪都是濕淋沐地,轉眼就結了冰,幾天下來,腳跟的肉也裂了,
凍瘡也大了,痛苦不堪,天天都要咬著牙根,流著淚水,一瘸一瘸的挑著水走在凹凸不平的泥石路上。
洗米要用冷水洗,冰凍的蝦要放在冷水裏化凍後剝皮,蔬菜要用冷水洗,十個手指都是麻麻地,剛把手放進剌骨地冷水裏在洗疏菜,外賣好了,
老先生怕冷,不願送外賣,一面喊一面催,叫我快去送外賣。送完回來,兩個手背紅腫成小餑餑,到了晚上又疼又癢,躺著捲曲在炕頭邊,就想起了家,
就想起了自己家的溫暖,就想起了父母的慈愛,禁不住淚水順著眼角像河堤決口般地在流淌著。
我在大邱小餐舘幹了一年,因我手拉麵拉出的麵條粗細均勻,並勤奮工作,很得到老板的賞識,在我辭工時,老板拉著我的手流露出依依不捨之情,頗令我感動。
我家從仁川搬遷到釜山後,我在自家餐舘又工作了快一年,經父親的鼓勵,我在插班考試中考取了初二,以十八歲的年齡,再度踏上求學之路。
十八,女大十八一朵花,我呢?我也是十八啊!
都曉生
|